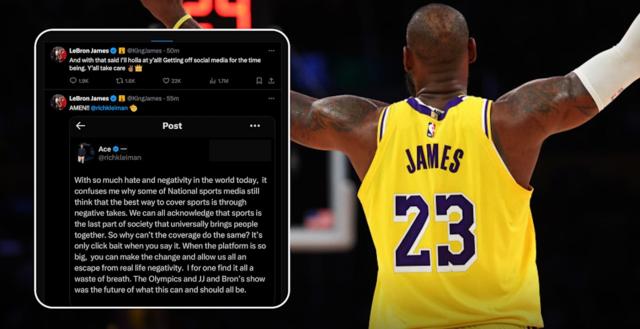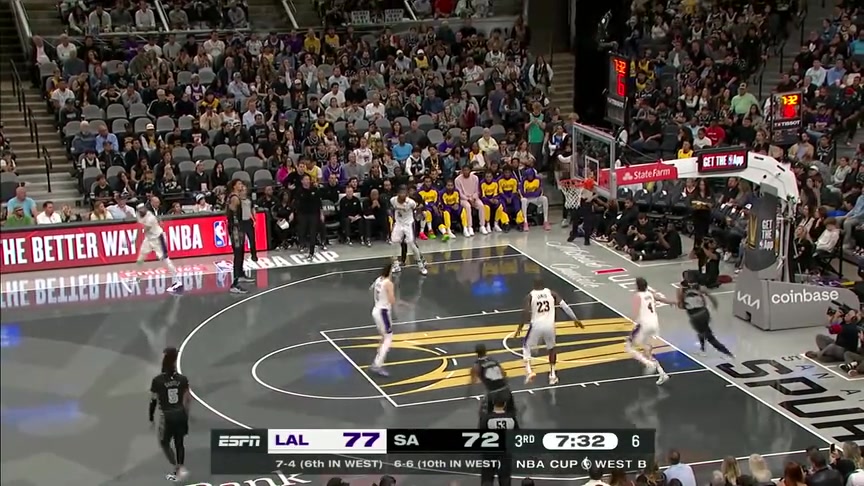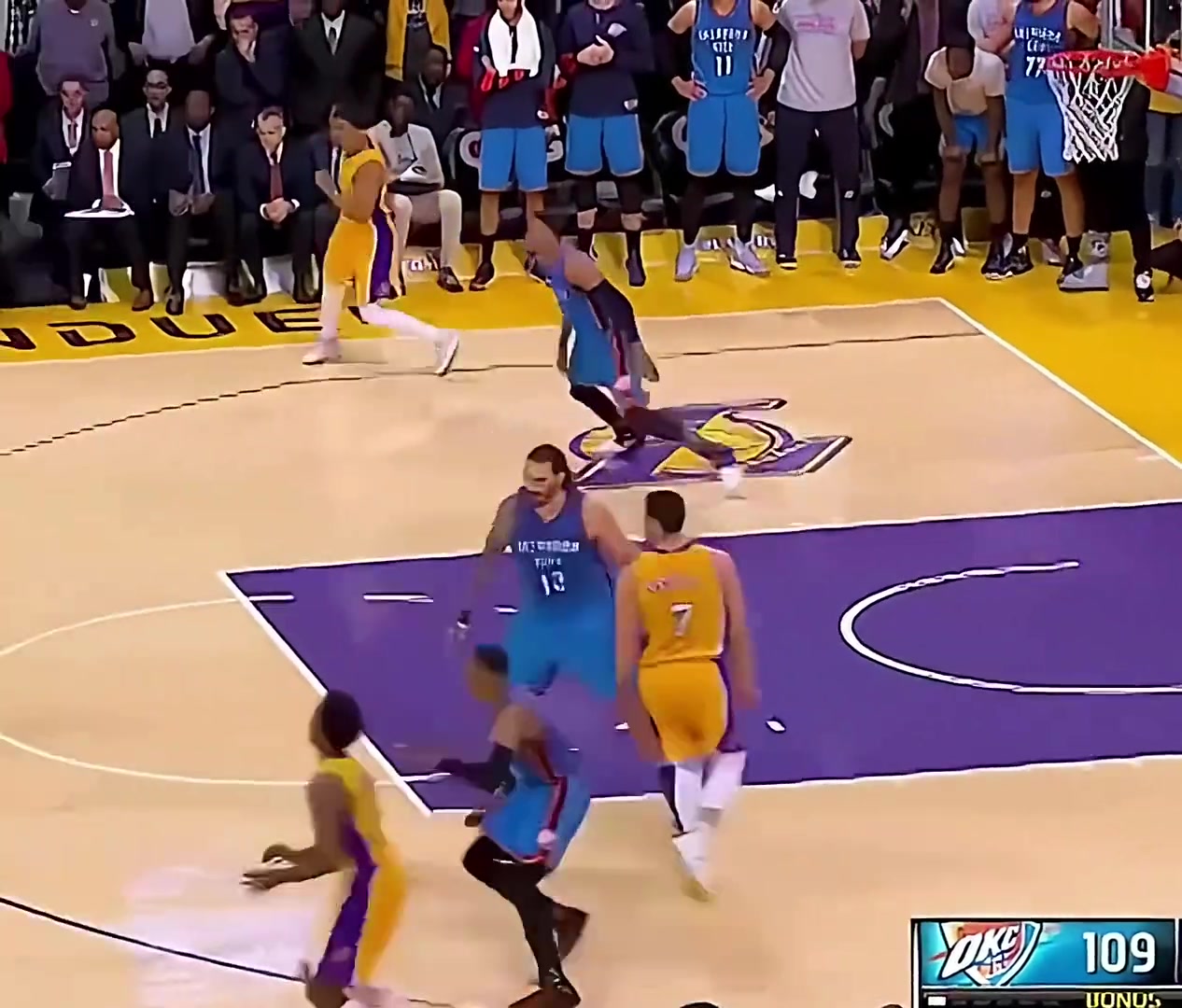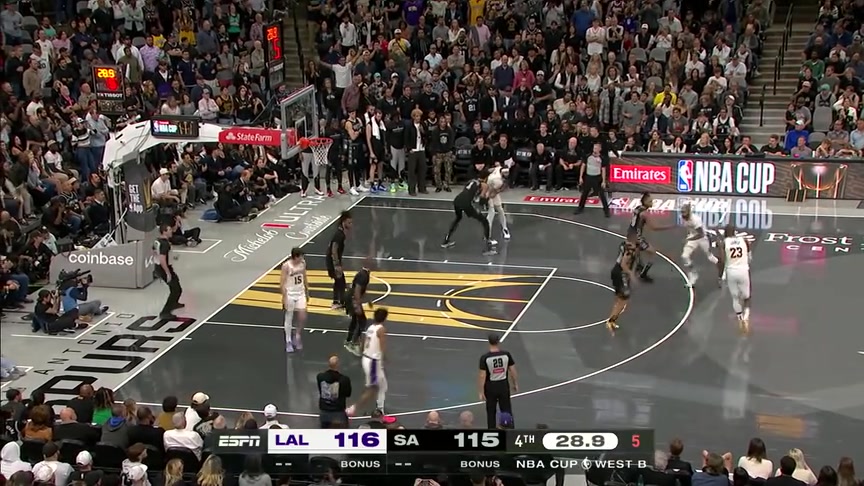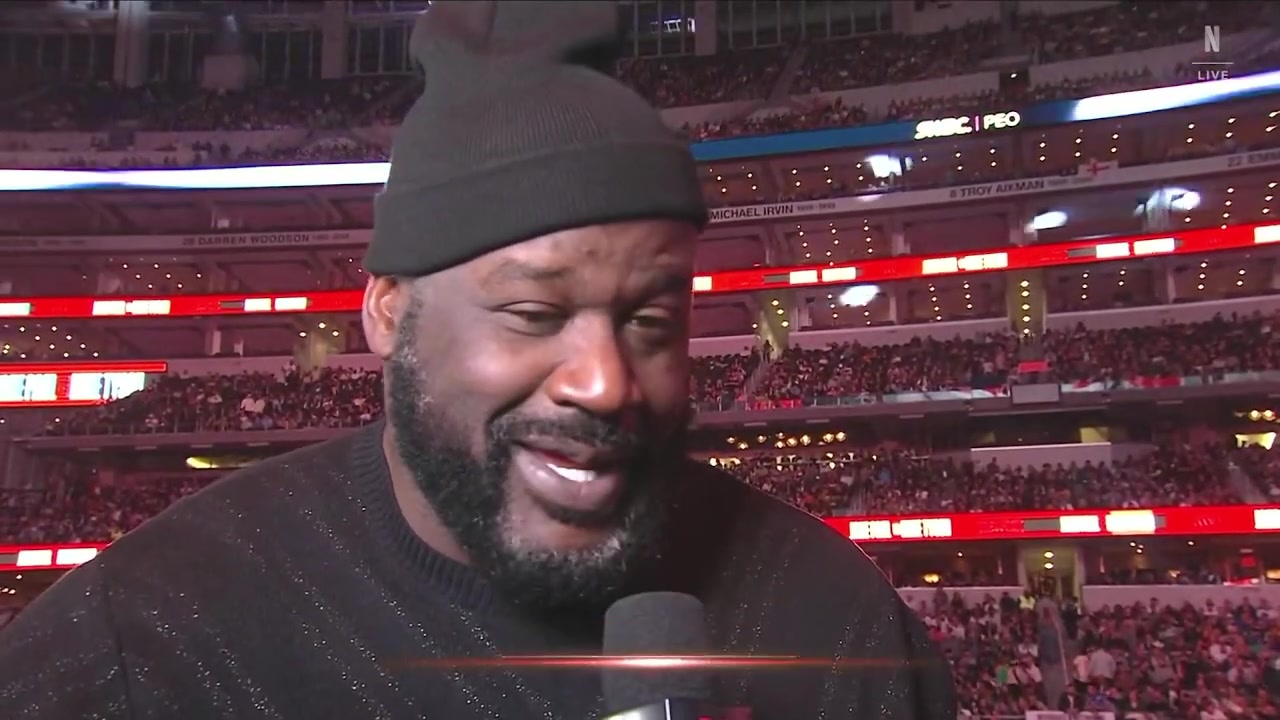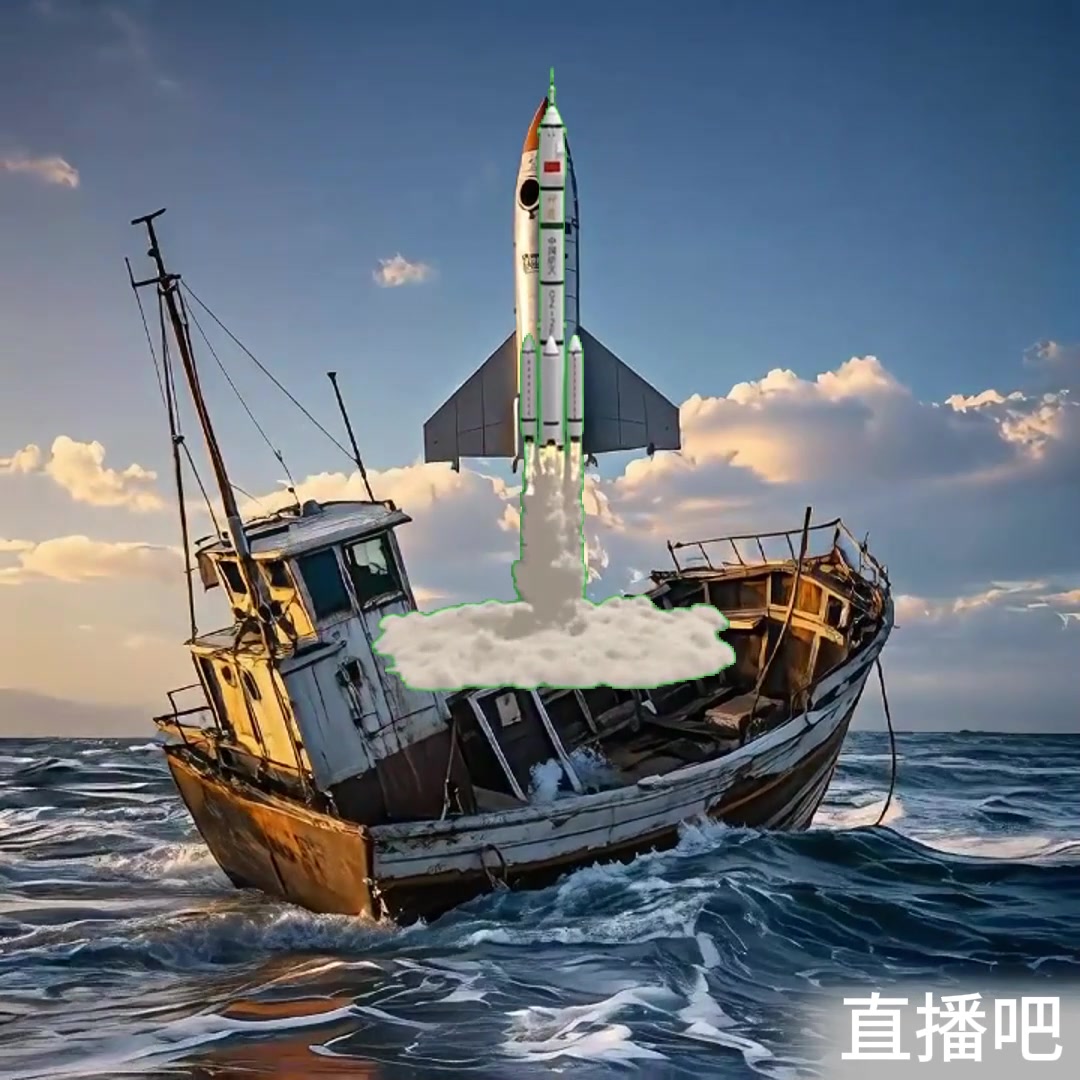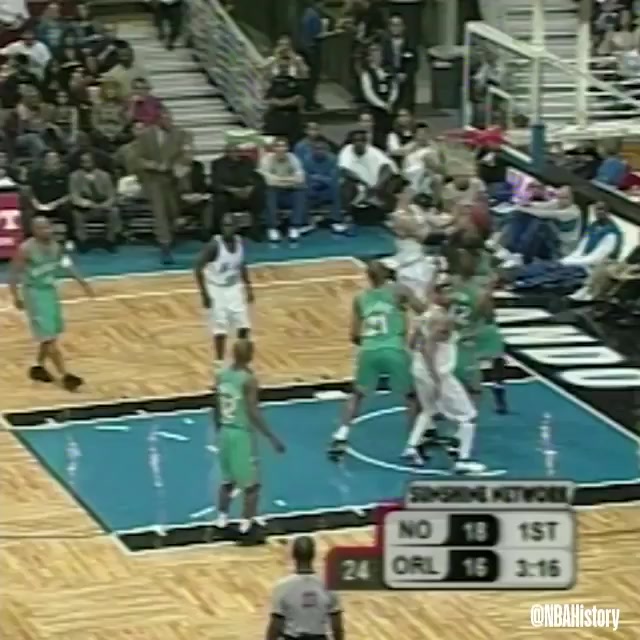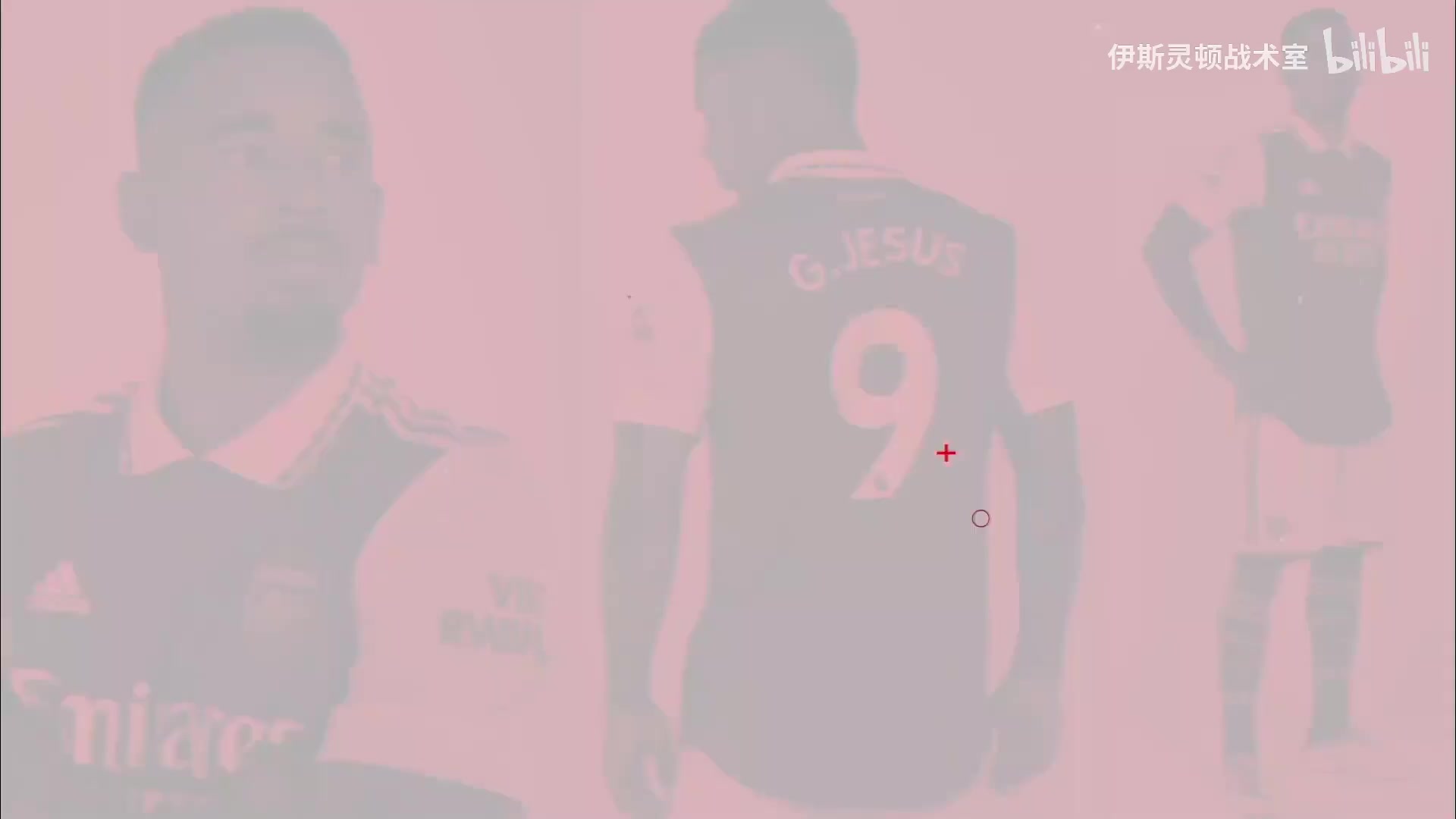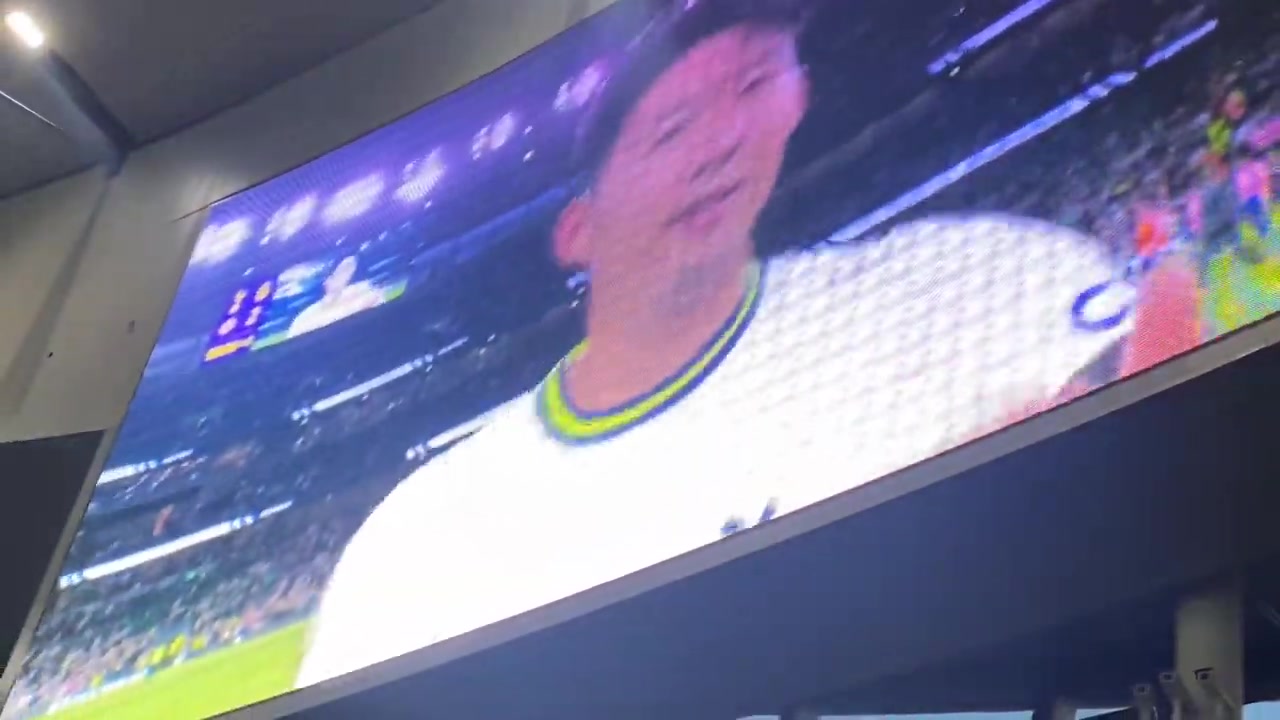【亲笔】保罗-乔治谈回家乡效力:在山的另一边

最让我感到疯狂的事就是死一般的寂静,仿佛整座球馆被抽真空了一样。可能因为我自己没缓过神,我依稀能听见观众席上球迷沉重的喘气声,即使他们都捂着脸我也能窥见手指缝间惊恐的表情。
训练师们跑向我倒地的位置,一开始我没感觉到不对劲,等我想要站起身,发现再怎么咬牙坚持都站不起来,当时我还没低下头看自己的腿。之后我便注意到现场的许多球迷拿出手机对着我拍个不停,还没弄清楚情况的我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低下头望向自己的腿……
上一秒,24岁的我随着美国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上征战,带领印第安纳步行者朝着总冠军再度发起冲击;下一秒,整个职业生涯在我眼前一闪而过,五味杂陈。有第一次入选十佳球的辉煌,有首次代表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比赛隔扣的画面……记得第一次来到凯尔特人主场北岸花园打比赛,看到凯文-加内特、拉简-隆多、保罗-皮尔斯、雷-阿伦和沙克-奥尼尔一块登场的时候,给我感觉就像看空中大灌篮里的怪物奇兵出场一样。
第一次和麦迪对位完,比赛结束后坐在更衣室里我一直在想:我刚才是和麦迪对位了吗?就像后来的我躺在球场上等着担架进场时,一直在想:我还能成为原来的保罗-乔治吗?好在那个夜晚,我的母亲就坐在观众席里,我们之间一直有着特殊的联系。后来母亲陪着我坐上救护车赶去医院,她一直在我耳边重复:“没事的孩子,一切都会没事的。”
这句话从母亲嘴里说出来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母亲的话让我充满了力量。因为她经历过真正的痛苦,我所承受的和小时候目睹母亲所承受的相比不值一提。在我六岁时,母亲得了中风还查出了血凝块,医生甚至都判了死刑。那时候我太小了,没有意识到母亲能战胜病魔活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在医生的积极治疗下,母亲之后几年的恢复进展快得惊人,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从鬼门关爬回来后,留下了部分瘫痪的后遗症,康复过程还需要继续和病魔作斗争,道路还很漫长。
记得我曾经在母亲医院的病床旁放了一把椅子,每个夜晚都握紧母亲的手,陪她一起入睡。医生允许她出院回家治疗后,我们在客厅搭了康复床,我在床边地上放了很多毯子和枕头,晚上就睡在母亲的旁边。当我在球场上摔断腿后,母亲也是这样在救护车里陪着我,握紧我的手,对我说:“没事的孩子,一切都会没事的。”
母亲不是在说空话,我真的相信她。康复过程中,抑郁、低落和沮丧在所难免,每当我需要坚持下去的力量时,就会找母亲聊天。她相信我能完全康复的,因为她清楚篮球是我这辈子真正想做的事情。如果不信,你可以去问她,她会告诉你我以前不舍昼夜地练习投篮的故事,穿着一身黑衣服光着脚,晚上十一点在雨中光着脚练习投篮的画面你能想象吗?倒不是买不起鞋子,而是练球让我过于兴奋,连30秒穿鞋的时间都不想浪费。我的姐姐可能会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我在全球性基督教青年社会服务团体打的第一场全场5V5比赛,其他的孩子都有全套篮球装备,而我穿着自制的短款牛仔裤就直接上场了,从膝盖处拿剪刀剪短而成的“运动牛仔裤”。
好像篮球消耗了我太多精力,以至于我不会去思考其他的事情,这种热爱已经近乎于病态。当我说自己专注于打球时,就真的是全身心投入进去,其余什么都不管。人们需要了解过去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如果你不是来自加州,那我就必须和你描述一下。贝弗利山庄和好莱坞知道吗?我们不是生活在那。好莱坞远处的山脉知道吗?我们住在山的另一边。
洛杉矶的另一边:羚羊谷的帕姆代尔,80年代的时候,许多家庭为了更好的生活从东南部英格尔伍德和康普顿地区搬到了帕姆代尔。那里就像一群蓝领工人生活的沙漠小镇,除了打球和逛商店没有别的事好做。2000年的时候,我才十岁,奥尼尔和科比带领洛杉矶湖人开启了三连冠王朝,年轻的快船涌现了迈尔斯、奥多姆和埃尔顿-布兰德这样的优秀球员。那是洛杉矶篮球的辉煌年代,而我家里人支持湖人和快船的比例大概五五开吧。
我绝对是科比的铁粉,很多比赛方式都在模仿他。而快船选中了从高中上来的天才达柳斯-迈尔斯,戴着白色头带用各种空接暴扣吸引你的眼球。湖人的科比当时是现役最伟大的球员,快船的魅力在于球队文化。我对洛杉矶篮球着了迷,当时你和我聊天的话,会发现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篮球。
姐姐塔奥莎比我大五岁,过去我们会在车道上玩。更正一下,不能在车道上玩,父亲在窗户前警告过我们不能因为玩篮球被车碰到。所以我们抱着球拿着移动篮筐到死胡同里单挑,那个篮筐很破,比你想象得还要破一点。链子快掉下来,杆子上缠满了黑色的电工胶带,很可怜的设施。不过我姐姐的技术太秀了,有邓肯一般的中距离跳投,三分线内、三分线外投篮都没问题,甚至还会打板,她是实打实的建队基石。一直到了高二我才击败她,之后我再也不愿意和她单挑了。
由于以前我不认识任何一位在大学打球的球员,所以并没有人来招募我。YouTube出现后,我看着那些来自纽约和洛杉矶在AAU打球的大家伙们的集锦,感觉他们和我生活的不是一个世界。兰斯-史蒂芬斯、德玛尔-德罗赞和朱-霍乐迪,这些和我年纪相仿的球员却比我出名得多。我没有AAU球队,也没有健身教练,不得不自己给自己疯狂地安排训练项目。有一年圣诞节,姐姐塔奥莎得到了弹跳训练鞋的圣诞礼物,我从她那借来,穿着这双鞋整天在社区里溜达,就像在宣告:我马上就要扣篮了,再过六个月肯定没问题。我会在包里装满石头到家后面的沙漠里奔跑,背着石头在蒲公英丛里做俯卧撑,没有iPod这样的设备,耳边只有飒飒的风声,这就是我的“健身中心”。

我想要到山的另一边去,希望自己能被球探发现,而且我知道自己不能失败,尤其是看到父亲在母亲生病时为家庭的付出。白天父亲在轮毂店工作,21世纪初期正式轮毂店的鼎盛时期,工作很忙。我长大些后,父亲开始兼职做木匠活挣更多钱,经常凌晨3点就出门了,忙到晚上7点才回家。回家之后,他还要去花园里忙活,带姐姐去逛商场,带我去钓鱼,现在想想父亲当时所承担的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看到父亲如此努力地挣钱养家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失败,实际上我等了很久才有了改变。直到高二我才被人发掘,这里我要感谢达娜和大卫-朋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在锦标赛上注意到我,随后邀请我去他们的AAU球队打球。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球队大名单里的一个位置,父亲为了挣钱养家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几乎工作满24小时,这次机会对我而言简直是救命稻草。没有人送我去洛杉矶另一边训练,达娜和朋普派车来接我,训练完晚上再送我回来,他们真的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他们,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这里给你们讲故事,我不可能进到NCAA,不可能被NBA选中,永远不可能拥有如今拥有的一切。那时候的我一点名气都没,第一次训练时队友们一脸迷惑地看着我,眼神里透露着:“这小子是谁?从哪里冒出来的?”而我看他们的眼神则是:“好吧,我认识你,我也认识你!”
刚刚过去的夏天很精彩,人们一直在对我说:“噢,你跟莱昂纳德早在AAU打球的时候就认识了。”就因为我们都来自洛杉矶,都加盟了快船吗?不,我和莱昂纳德在AAU的时候毫无交集,直到打了大学联赛我才算认识了莱昂纳德,他效力圣迭戈州立大学。
其实我们应该在大一赛季的勒布朗训练营上就认识了,当时训练营里的每个人都在讨论他,称莱昂纳德貌似是个打得很好的球员。结果前两天他都没来,关于他的传闻甚嚣尘上,称神秘的莱昂纳德是个超级厉害的球员。再然后我就因伤退出了训练营,一直到大二赛季要和圣迭戈州立大学打比赛前都没再想过他。比赛前我看了一下对手的出场名单,前锋的位置上我看到卡哇伊-莱昂纳德,突然记起来这个神秘的球员,同时也在纳闷:他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有些人,真的天生就自带光环。莱昂纳德出场热身了,我的目光就锁定在他身上了。从跳球开始我们一整晚都互相盯着对方,我打得很努力,那是疯狂的一个夜晚。莱昂纳德整场比赛一个字没说,但气场强大到令人发指,赛后我向他投去了肯定的目光:“好吧,的确非同一般,你很强!”我想眼神交流是和他沟通最好的方法。那天晚上坐在场边的球迷可能怎样都想不到,这两位来自洛杉矶郊区的孩子之间的对决,会在NBA的舞台上重演,两位被低估的孩子也成为了NBA全明星。时隔多年,我和莱昂纳德在同一支球队相聚,一起回到了家乡。
回顾整个职业生涯,从AAU联盟到加州大学弗雷斯诺分校,最佳新秀阵容、最快进步球员,在印第安纳入选全明星又辗转到了俄克拉荷马。不行,我得暂停一下,我想说我很爱很爱很爱俄克拉荷马的球迷,能在他们面前打球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自从我初次抵达俄克拉荷马下飞机的那一刻,那里的球迷就张开了怀抱欢迎我,我和威斯布鲁克也有着很好的默契,这在商业化的联盟里是很少见的,我珍惜在俄克拉荷马打球的时光。
能有机会回到洛杉矶,为家乡球队效力同样不可思议。十年前离开家乡去大学打球时,家里没有人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还记得父母第一次接到经纪人电话,得知我的名字出现在热门首轮秀中时,他们有多震惊和激动。他们曾经为了看我在弗雷斯诺的每场主场比赛,每周二从帕姆代尔开车三个多小时到弗雷斯诺,来回七个小时车程只是为了亲眼看我在场上打球。我在他们眼里永远都是那个拖着破烂球框光着脚到死胡同里打球的孩子,一切似乎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般。
这就是为什么休赛期我会激动地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将回到洛杉矶为快船队打球,我不寄希望于外界能理解我的用心,我清楚母亲最近几年长途跋涉看我打球有多么辛苦。她是我的勇士,从不抱怨,我很幸运能成为她的孩子。坐飞机折腾对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好在现在父亲能开着车载她来斯台普斯中心看我打球了,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
其实准确地说,洛杉矶不是我的家乡,我来自洛杉矶的另一边,我为此感到骄傲。曾经的我背着石头在沙漠里奔跑,希望有人能注意到我,希望我能跑到山的另一边,跑进斯台普斯中心,站在聚光灯下享受球迷的欢呼。
洛杉矶不仅仅是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我还想代表孕育过我的那部分洛杉矶。我想要胜利,想要总冠军,想要为所有的洛杉矶带来一枚总冠军戒指,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
原文:Paul George

编译:晴天
相关阅读: